
昨天在刷到一个非常简短的短视频,是付航脱口秀中的一个观众互动。
付航问:你听过最假的一句话是什么?
观众:「妈不爱吃」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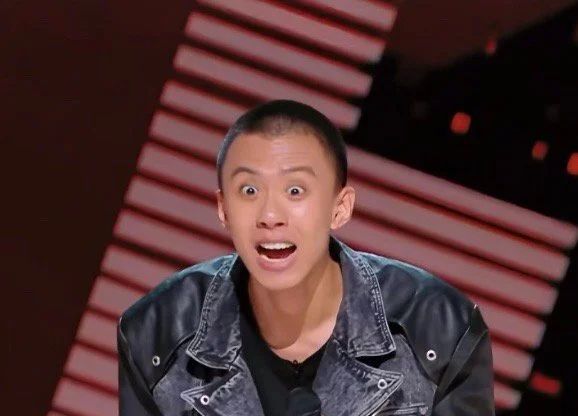
这让我想到费兰特在《烦人的爱》里,当小说情节揭开童年,主人公自己撒的谎言时,她说到:「童年是个谎言的工厂」。
是啊,每个人的童年,由于各种各样儿童无法理解的原因,我们蒙蔽在各种各样的谎言里。小时候,儿童信以为真,以为妈妈真的不爱吃。但总有一天,我们回头发现,或许是自己做了爸妈之后,或许是逐渐独立生活时,我们有了从家庭外部视角观察妈妈后,我们意识到,「妈不爱吃」是个狗屁谎言。
当初被谎言掩盖的内疚感,在多年之后爆发。
掩盖内疚感的谎言,还稍许健康,如克莱因所说,内疚性焦虑是抑郁位的特征。
还有另一些谎言,更加隐秘而难以言说。
「你不要晚上出门,门外有大灰狼会把你吃掉」。
「不要出国,国外都是动乱,哪里还会比我们国家好吗」。
「不要离开体制内工作,资本家会给你好日子过?」。
这是另一类谎言。这个谎言很隐秘、复杂和模糊,因为它是以爱和关怀的名义发起的,它其中包含着真实的真诚,但却把某种恍惚的幻象植入其中了。
很多人长大到30多岁,更不幸的人可能终其一生,都无法识别和区分,这句话中真诚的部分,和谎言的部分。
识别这类谎言,要回到它最初的起点:「你不要晚上出门,门外有大灰狼会把你吃掉」。
这句话翻译成最真诚的版本来说,是「你晚上出门,妈妈需要陪你一起出去,可是妈妈上了一天班很累了,不想出门了。你自己一个人出去又不安全,今天就不出去了,好吗?」
在它最原初的版本里,有一个比较现实的内容,对于一个五六七八岁的儿童来说,一个人出门的确不安全,而拒绝这个儿童出门,可能引起ta的愤怒、反抗和受挫,去消化和安抚这种复杂的情绪,给妈妈带来太大的负担。一个简单的“迫害性”谎言,可以比较轻松简单地说服儿童。
这类谎言的日复一日,阉割了一个儿童的扩张性和探索世界的好奇心。慢慢地,儿童开始自我欺骗——「世界很危险,我要乖乖待着妈妈身边」,「我很弱小,不待在妈妈身边,我会受伤害」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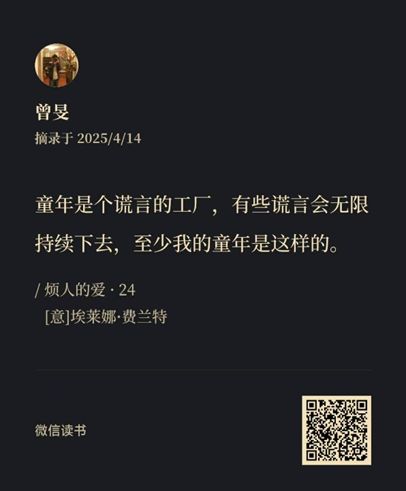
这个谎言不会消失,就像费兰特所说,「有些谎言会无限持续下去」。童年的谎言会变成一种自我催眠和自我对话,哪怕你三十岁、四十岁、五十岁,你心底里依然保留着三四五六岁时,坚信的人生信条——或许不再是当初听到的“原版”,而是经过你日后生活经验修改的版本。
但那个“谎言”的本质没有改变——「大灰狼」的故事会成为“迫害性”的阉割力量,哪怕你只是站在一个从没去过的新的餐厅门口时,这股力量也会隐秘地发声说:「不要尝试新的东西,新的东西里有“大灰狼”,可能让你吃亏!」
一次次自我确认的过程,让自体感更强壮,你可能会鼓起勇气,去挑战这个“谎言”,尝试和它温柔地对话:“真的吗?真有那么可怕吗?我想试试。”
但可能有些人没能在成长过程中,被他人确认过自我,他们的自体脆弱、空虚,内在并不结实,于是没有勇气去挑战那些“童年的谎言”。
于是,会出现两种极端的反应,在其中一端是完全的自我阉割,碌碌无为的活在安全里,恍恍惚惚、迷迷瞪瞪,倒也安安稳稳的度过了这一生。没什么事情发生,也没什么活力和趣味,在一种无聊和无生机的状况里。
在另一端,是完全的破坏和不管不顾,“你骗我!我恨你!”。带着这种被欺骗的、突然恍然大悟的震惊感,以惊人的震撼和仇恨,义无反顾、歇斯底里地报复回去——我要坚决和“童年的谎言”决裂!我要活出另一番样子。
这一端的决裂,会演变成一种自我放逐,曾经自我生长的营养,被一次性倾倒出去,自我变得空虚而贫瘠。这种空虚和贫瘠又会让人“误以为”是世界剥夺了我,以至于此。
这两端的摆荡会像激烈的钟摆,一时愤恨、攻击、仇恨,于是看似充满活力,要和这个世界大干一仗,一时又陷入瘫软无力、抑郁、空虚的无聊中,好像之前发起的那场盛大的冲锋,发现自己扑空了,什么也没有得到。
在多次摆荡之后,人们可能会逐渐回归到中间。看清这“童年谎言”的两股力量——妈妈的善意和无力,从而内疚开始滋生——原来妈妈已经尽力了,她只是不知道如何是好。
人们开始尝试和“童年的谎言”对话,而不再只是活在曾经的“杀戮时刻”里——一方要干掉另一方的意愿和情感。
当我们回头,从另一个角度看,这里并没有什么谎言,有的只是,当时那个儿童对于ta决不能背叛的那个人的绝对忠诚。
作者简介:曾旻Zeng Min,个人执业心理咨询师,心理动力学取向;北师大心理学硕士、P1国际心理治疗研究院长程受训;个案经验2500+小时:持续接受督导与个人体验。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: 曾旻ZengMin(ID:zengminpsy),这个世界上永远没有相互理解,你眼中的我,也只是你想要看到的我。
本文转自壹心理